下一個Transformer可能又被Google做出來了
如果把現在的頂尖大模型比作一個人,那它一定患有一種罕見的神經系統疾病:順行性遺忘症(Anterograde Amne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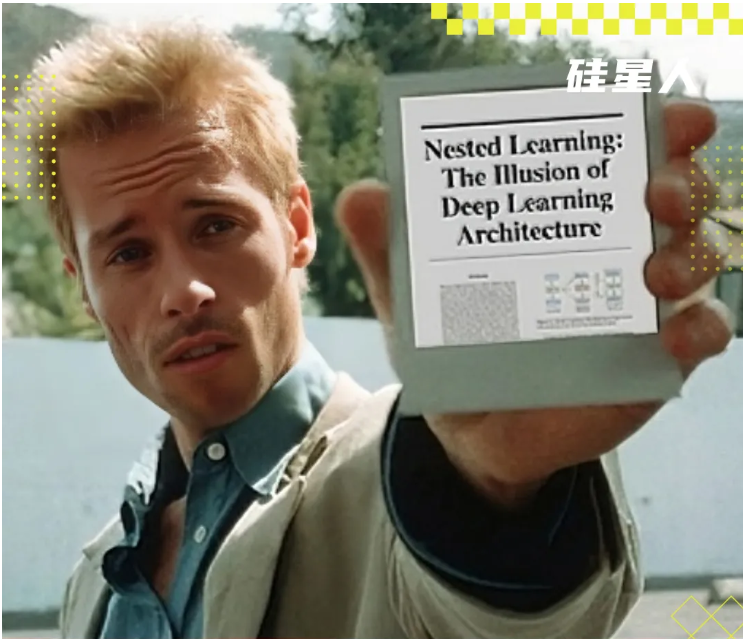
這是 Google Research 研究員、最近最受關注的一篇論文《Nested Learning: The Illusion of Deep Learning Architectures》第一作者 Ali Behrouz 拋出的一個讓所有人陷入沉思的比喻。
看過諾蘭的電影《記憶碎片》(Memento)的人更能理解這種絕望。這種病症的患者擁有完好的“過往記憶”(Retrograde Memory),他們記得發病前的一切,我是誰,我來自那裡,我有什麼技能。但對於發病後發生的所有事情,他們永遠無法形成“新的長期記憶”。他們只能活在短暫的“當下”,幾分鐘後,一切就會被重設。
這就是現在 AI 模型的真實寫照。
無論Gemini或是ChatGPT多麼博學,如果不聯網搜尋,它們都只能依靠預訓練階段獲得的出廠知識(也就是“發病前”的記憶)來回答問題。而在對話窗口裡,無論你教給它多少新公司的業務邏輯,或者糾正了它多少次程式碼錯誤,這些資訊都只停留在短暫的上下文窗口裡。
一旦窗口關閉,或者視訊記憶體被重設,它就像金魚一樣,把剛才發生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 。下一次見面,它依然是那個出廠時的它,絲毫沒有因為與你的互動而變得更聰明一點。
為什麼擁有超級算力的 AI,卻治不好這個健忘症?
長期以來,行業有一種二元對立的看法,認為 AI 的“架構”(Architecture)和“最佳化器”(Optimizer)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物種。
架構是骨架(如 Transformer),它是靜態的,出廠即凍結,負責“推理”。“最佳化器”是雕刻刀(如 Adam、SGD),它是動態的,只在工廠裡用來訓練模型,出廠後就被沒收了。
我們習慣了把 AI 當作一個靜態產品,訓練好了,打包發佈,使用者只管用。
但在 Google 最新發佈的 52 頁硬核論文《Nested Learning: The Illusion of Deep Learning Architectures》(巢狀學習:深度學習架構的幻覺)中,研究團隊試圖告訴我們,這其實是一種幻覺,是我們人為製造的自我設限。
如果架構和最佳化器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呢?如果並沒有所謂的“訓練階段”和“推理階段”之分,一切都只是不同頻率的“記憶壓縮”過程呢?
基於這個大膽的假設,Google 團隊提出了一個名為 HOPE 的新框架。他們並沒有簡單地堆砌參數,而是試圖從底層邏輯上重構 AI 的“大腦結構”,讓它不再是一個出廠即固化的工具,而是在每一次互動中都能微調自己、擁有“快慢記憶系統”的動態生命體。
而這篇論文也被不少人稱為“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V2”,這篇論文提出的Transformer 架構成就了今天大模型的火熱,而HOPE讓人們期待它成為下一個Transformer 等級的創新。
拆解“幻覺”:被遺忘的中間地帶
要治好“健忘症”,我們首先得看看現在的 AI 大腦裡到底裝了什麼。
在 Ali Behrouz 的解構下,目前的 Transformer 架構呈現出一種極端的“精神分裂”狀態。如果不使用複雜的數學術語,我們可以把它的內部元件看作兩個極端:
一個是“極快”的 Attention(注意力機制)。它時刻處於亢奮狀態,對你輸入的每一個字(Token)都進行瞬時的計算和響應。它的更新頻率幾乎是無限的,這讓模型擁有了所謂的上下文學習能力(In-Context Learning),你剛說的話,它馬上就能用。
另一個是“極慢”的 MLP(前饋神經網路)。它是模型的長期記憶庫,承載了絕大多數參數。但它的更新頻率是 0。這部分像一塊凍結的硬碟,除非你耗費巨資進行全量微調(Fine-tuning),否則它永遠不會改變。
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真空地帶。
這就是“幻覺”的根源。人類的大腦並不是這樣工作的。我們的記憶是一個連續的頻譜,我們有幾秒鐘的感官記憶,有幾小時的工作記憶,也有幾天甚至幾年的長期記憶。我們的腦突觸並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以各種不同的頻率在不斷微調。
為了填補這個真空,Google 團隊提出了 Nested Learning(巢狀學習) 的概念。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套精密咬合的齒輪系統”:
- 最外層的小齒輪轉得飛快(處理當前的對話);
- 中間層的齒輪轉得稍慢(記住過去幾小時或幾天的任務);
- 最裡層的大齒輪轉得極慢(沉澱世界觀和基礎知識)。
為了證明這種統一性在生物學上的合理性,他甚至在論文中引用了一個非常硬核的神經科學案例,半球切除術(Hemispherectomy) 。
醫學發現,即使切掉人類的一半大腦,通常是為了治療嚴重癲癇,剩下的一半腦組織也能通過重組資源,接管幾乎所有功能,人依然能正常生活。這說明大腦並沒有什麼“專門負責 Attention 的模組”或“專門負責 MLP 的模組”,神經組織是通用的、可復用的。
同樣的道理,AI 的“架構”和“最佳化器”本質上也是同一種東西,只是處於不同的巢狀層級:
- 傳統的模型記憶的是“資料”(Token);
- 最佳化器(如 Adam)記憶的是“梯度”(Gradient)。即“我上次在這個地方犯了錯,下次要修正” 。
既然都是在“記憶資訊”並“更新狀態”,為什麼我們要把它們人為地割裂開來?也許我們不需要在這個二元對立的框架裡修修補補,可以直接設計一個全頻率覆蓋的動態系統。
HOPE 的三層設計
基於 Nested Learning 的理論,Google 團隊交出了一份具體的工程答卷,還起了一個充滿寓意的名字:HOPE (High-order OPtimization and Expressivity)。
如果說傳統的 Transformer 是一個只有短期記憶的“單核處理器”,那麼 HOPE 更像是一個符合神經科學原理的“雙重記憶大腦”。它通過兩個元件,復刻了類似生物大腦中海馬體(Hippocampus)與大腦皮層(Cortex)的協作機制 。
1. 快系統:像海馬體一樣敏銳的 Titans
在 HOPE 的最前端,是處理即時資訊的“快系統”。這裡 Google 使用了論文一作 Ali Behrouz 之前的另一項成名作Titans。
你可以把 Titans 理解為一種“超級 RNN”。它就像人類靈活的海馬體,負責快速捕捉和編碼當下的新知。傳統的 AI 模型在處理新資訊時是被動的,但 HOPE 裡的 Titans 模組具有極強的“主觀能動性”,它是 Self-Modifying(自我修改) 的。
它不僅是在讀取資料,更是在根據當前的上下文,即時生成自己這一步學習所需要的 Key、Value,甚至自己決定這一次記憶的 Learning Rate(學習率) 。這意味著,它能敏銳地判斷眼前資訊的重要性,快速形成短期記憶。
2. 慢系統:像皮層一樣厚重的 CMS
這是整個架構中最具顛覆性的設計。HOPE 引入了 Continuum Memory System (連續記憶系統,CMS)。CMS 就像是厚重的大腦皮層,負責將經過篩選的知識長久地刻印在神經元中。
在 CMS 中,模型內部的 MLP(前饋網路)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被切分成了不同的層級,就像不同轉速的齒輪:
- 高頻層: 可能每處理幾百個字就更新一次,用於捕捉剛才對話裡的新定義。
- 中頻層: 可能每處理幾萬字更新一次,用於適應一個新的項目背景。
- 低頻層: 幾乎不更新,用於穩固語言的語法和常識 。
這種設計避免了災難性遺忘。當新知識湧入時,它會被優先儲存在高頻層,而不會去驚擾低頻層裡的舊知識。隨著時間的推移,真正重要的資訊才會像沙漏裡的沙子一樣,慢慢沉澱到深層。
3. 最佳化器也有了“記憶”
Google 的激進之處在於,他們不僅改造了大腦(架構),還改造了老師(最佳化器)。
為了配合這就這套複雜的系統,他們設計了一個名為 M3 (Multi-scale Momentum Muon) 的新最佳化器。
既然模型分了層,最佳化器為什麼不能分層?普通的 Adam 最佳化器只看眼前的梯度(Local Structure),容易陷入短視。而 M3 最佳化器本身也被設計成了巢狀結構,它有一層“快動量”負責看腳下的路,還有一層“慢動量”負責看遠處的山脈(全域 Loss Landscape)。
這意味著,連負責訓練的演算法本身,都擁有了更深遠的記憶力。
實驗資料顯示,這種設計在 ImageNet 和大語言模型訓練上,不僅收斂更快,而且最終效果更好。
4. 給工程師的“後悔藥”
對於工業界的開發者來說,HOPE 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從頭訓練一個新模型,而是它提供了一種“原地改造”的可能性。
Ali Behrouz 在分享中提到了一個名為 Ad-hoc Level Stacking 的技巧,你不需要拋棄手裡現有的 Llama 或 Qwen 模型。你可以直接拿來一個預訓練好的模型,人為地將它的不同層指定為不同的“更新頻率”,把淺層設為高頻,深層設為低頻 。
這就像是給一輛已經出廠的舊車,通過刷新韌體就解鎖了自動駕駛功能。這一特性,讓 Nested Learning 成為了一個工程方案。
從“靜態產品”到“動態生命”
我們把視角從程式碼行中抽離出來,會發現 Nested Learning 真正的野心,不在於刷榜,而在於試圖完成一次 AI 領域的範式轉移。
在 NeurIPS 的分享最後,作者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深度(Depth)也許不再是唯一的答案。”
過去十年,我們一直在堆疊物理層數,把神經網路做得越來越深。這種暴力美學確實帶來了湧現能力,但它也製造了一個巨大的“幻覺”,誤以為智能來源於靜態的深度。而忽略了真正的深度可能來自於巢狀的最佳化。
更進一步,論文中提出了一個極其激進的定義:“預訓練本身,其實就是一種超長上下文的 In-Context Learning。”
這句話消解了 AI 領域最大的邊界。在 Nested Learning 的願景裡,沒有所謂的“訓練結束”這一天。模型在與使用者互動的每一秒,都在以某種微小的頻率更新自己的突觸。它不再是一個冰冷的、出廠即固化機器,而是一個在資料流中不斷呼吸、代謝、進化的有機體。
這或許才是通往 AGI更本質的道路,智能不是被灌輸的,而是在互動中生長的。
當然,任何試圖顛覆範式的理論,註定會伴隨著巨大的爭議。這圍繞這篇論文討論區裡,聲音很多樣。
樂觀者將其視為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V2"。社區對於自我修改這一概念尤為著迷。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詬病 LLM 只是“統計學的鸚鵡”,而 HOPE 讓 AI 第一次擁有了某種“元認知”能力,即學習如何學習。這種從被動擬合到主動適應的跨越,被認為是 AI 產生質變的關鍵。
實用主義者則看到瞭解決災難性遺忘的曙光。如果這一架構能落地,未來的企業級 AI 將不再需要為了更新一點點業務知識而耗資百萬進行全量重訓,AI 可以在業務流中自然地學會新規章,同時不忘記舊制度。這是對降本增效是最直接的。
質疑者也大有人在。比如有評論指出,論文中將 SGD(梯度下降)強行解釋為“聯想記憶”的數學證明雖然精彩,但更多依賴直覺,缺乏嚴謹的收斂性保障。更有工程師擔心,這種複雜的“巢狀最佳化”會讓調參難度呈指數級上升,畢竟,調一個 Adam 已經夠頭疼了,現在我們要同時調好幾個不同頻率的“大腦”。
但無論如何,Google 這一次沒有在參數量上卷,而是在“學習的本質”上開了一槍。
它用一種近乎哲學的方式提醒我們,對於一個真正的智能體來說,存在就是壓縮,活著就是學習。 (矽星人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