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鴉文化的生命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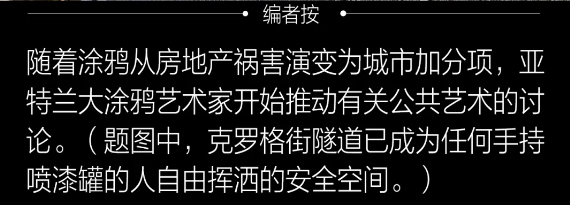
遍佈塗鴉的克羅格街隧道(Krog Street Tunnel)體現了新舊亞特蘭大的碰撞。隧道的一端距離民權運動傳奇人物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出生的甜奧本區和他的墓地僅幾個街區。另一端則是曾經的工人區椰菜鎮(Cabbagetown)和由被解放的黑人農奴創立的雷諾茲鎮(Reynoldstown),這兩個社區都經歷了劇烈變遷。
隧道內外的牆壁上留下了該地區不同歷程階段的印記,它們以塗抹、刻畫、標語、記號和噴漆的形式層層疊加,時間戳可追溯至幾十年前。生存是這些印記的主線。
克羅格街是亞特蘭大的幾處可供塗鴉藝術家(以及任何手持噴漆罐的人)自由揮灑的安全空間之一。居民們不僅接納了這些隧道塗鴉,還提供了更多牆壁,歡迎公眾創作和欣賞塗鴉。
這反映出這座城市對塗鴉採取了一種非官方的容忍態度。在亞特蘭大的大部分地區,你都能找到複雜精美的塗鴉牆。基於備受爭議的“破窗理論”政策,此類行為一度是執法部門的打擊重點。但今天,儘管塗鴉在亞特蘭大大部分地區仍屬非法,但側重點已經改變。正如全球許多城市一樣,塗鴉已成為城市機理的組成部分:過去被視為房地產禍害,現在則普遍被視為一種資產。
在亞特蘭大,塗鴉藝術家多年來一直在幕後推動對這一文化的保護和除罪化。
“這個文化需要被記錄下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在記錄亞特蘭大和紐約市塗鴉場景的安塔爾·“科爾”·菲爾斯(Antar “Cole” Fierce)說,“人們需要知道最早從事這項活動的是黑人孩子和拉美裔孩子。因為一百年後這個故事可能會被改寫,尤其是考慮到現在人們開始擁抱它。”
自人類掌握標記工具以來,塗鴉就一直存在。在美國,最早的塗鴉可追溯至內戰時期,當時南北兩軍的士兵在許多地點留下了塗鴉,喬治梅森大學正在北弗吉尼亞州籌備一個記錄這些塗鴉的數字檔案館。長久以來,塗鴉都講述著在某個地方、某個時間、某種情境下生活的人的故事。
然而,至少自20世紀中葉以來,城市領導者和傳統藝術組織開始通過犯罪視角看待塗鴉,經常將其與幫派活動關聯起來。雖然在某些地點和背景中,這種關聯的確存在,但更多的塗鴉還是來自於沒有幫派瓜葛的街頭藝術家。事實上,它被視為嘻哈文化的一個基本元素,而嘻哈文化曾在上世紀70年代有效促成了布朗克斯的幫派停戰。
這種停戰未能阻止80年代的紐約市長埃德·科赫(Ed Koch)進一步升級了前任們在70年代打響的反塗鴉戰爭。這場鎮壓導致了大規模監禁、警察暴行甚至死亡事件。但它未能阻止塗鴉傳播到亞特蘭大這樣的城市,如今,這座城市已被視為南方藝術字型(style-writing)風格塗鴉的聖地。
今年早些時候,電影製作人威爾·費金斯(Will Feagins)推出了紀錄片《眾王之城》(City of Kings),菲爾斯和幾位本地藝術家在片中展示和講述了亞特蘭大塗鴉文化的歷史。該片最近參加了羅馬舉行的嘻哈電影節(Hip Hop Cinefest)。費金斯說這部電影展示了在城市牆壁上噴繪狂野街頭書法的人更“私人的一面”。
“他們的創作熱情恰好不被許多人認可,這並不表示他們就是壞人,”費金斯說,“我看到了塗鴉與公共藝術之間的聯絡,我也希望幫助觀眾瞭解它們是如何關聯起來的。”
這種文化在多個城市取得了突破,例如有溫伍德塗鴉牆和塗鴉博物館的邁阿密,那裡可以說是城市接納的現代塗鴉運動的起點;以及費城,我們今天所知的塗鴉文化正是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費城。
為了讓塗鴉在亞特蘭大保留一席之地,菲爾斯將求助的橄欖枝伸向了一個曾被許多人認為會加快塗鴉文化消亡的實體:亞特蘭大環線(The Atlanta BeltLine),它過去是一條22英里(約35公里)長的環線鐵路,如今正改造為環繞城市的步行和自行車道。雖然該項目為這個嚴重依賴汽車的城市提供了急需的替代交通和休閒方式,但它也引發了人們對住房負擔惡化及黑人地標消失的擔憂。
儘管如此,這條環線實際上成為了塗鴉文化的生命線,幫助保護了克羅格街隧道這樣的場所,讓藝術字型塗鴉師們得以繼續創作。
“環線上的塗鴉將繼續存在,即使在未來的路線開發中也是如此,”亞特蘭大環線公司(Atlanta BeltLine Inc.)的發言人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表示,“當這條22英里長的環線於2030年完工時,我們的組織目標是確保在項目之前以及項目開始後為之做出貢獻的藝術字型塗鴉師的作品都會保留下來,以展示亞特蘭大的傳統、創造力和文化。”
克羅格街開放給公眾進行塗鴉,但環線上也有一些受保護的塗鴉地點。“索索迪夫塗鴉牆”(So So Def Walls)即其中一個神聖場所,普通人禁止觸碰,甚至多數藝術字型塗鴉師也需要特別邀請才能在此創作。邀請只能來自於塗鴉牆的創始塗鴉師“SAVE”,以及如今的官方守護者利維爾·“詩人”·懷特(Reveal “Poest” White)。
“索索迪夫塗鴉牆”得名於附近一塊曾經很有名的廣告牌,上面宣傳著傳奇的索索迪夫(So So Def)唱片公司。這些塗鴉牆位於75/85高速公路下方,過去無法輕易靠近,塗鴉師們必須穿過亞特蘭大警察局的一片扣留財物存放區,再穿過濃密的雜草、毒藤和灌木叢,才能抵達。
然而,自從環線清理了通往該地點的道路後,如今經常有人在這裡慢跑和騎行,牆上開始出現一些隨機塗抹,甚至被塗鴉師們視為了蓄意的破壞行為。牆上的塗鴉藝術可追溯至90年代,由本地和遠至加州甚至海外的藝術家受邀創作。
懷特說他最近花了大量時間清理未經許可的標語,特別是反對該市即將打造的公共培訓中心的反“警察城市”資訊。儘管反“警察城市”和“保衛森林”的標語出現在了城市各地,但懷特說它們寫在了預留給塗鴉老手的保護區域,覆蓋了之前的作品。
“我不得不直接去找他們的團隊,告訴他們‘拜託,別這樣幹’,”懷特說,“你不能說這是為了表達你的聲音,而為了讓你的聲音被聽到,你卻在壓制別人的聲音。這樣可不行。”
早在環線項目啟動前很久,懷特和菲爾斯已經開始致力於保護這些塗鴉牆。為了讓環線項目方認可這個區域的價值,他們必須爭取當時的環線藝術總監米蘭達·凱爾(Miranda Kyle)的支援,她也成為了一個有力盟友。作為專注於“文化場所保護與場所營造”的公共藝術活動家,凱爾將藝術字型塗鴉師的困境視為其更大使命的一部分:挑戰關於誰有權決定什麼是正當藝術以及什麼可以佔據公共空間的政策。
“這個空間之所以如此神聖,是因為從城市歷史的角度看,包括紅線的劃定,(75/85)高速公路建設時大量社區被隔離和摧毀,”凱爾說,“我認為索索迪夫塗鴉牆是一種對空間和身份的回收,是一個“我們不會被抹去”的宣言,這呼應了我的政治理念。”
懷特罕見地(堪稱顛覆性地)公開了他的真名,並成為了這條保護陣線的代言人。這很冒險,大多數塗鴉師為避免被警察抓捕,都會隱瞞自己的身份。此外,亞特蘭大藝術字型塗鴉師協會(Atlanta Style Writers Association)宣告成立,部分宗旨是為那些希望在宣傳作品的同時保持匿名的藝術家提供掩護。
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塗鴉師和環線項目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夥伴關係,沿途的幾個區域要麼被保留下來,要麼被創造出來,以延續塗鴉的傳統。亞特蘭大藝術字型塗鴉師協會網站上也在地圖中列出了其中幾個地點。目前環線項目為懷特提供資助,以維護塗鴉牆及開展相關活動。
“這對亞特蘭大來說意義重大,我不能容許它被遺忘,”懷特說,“所以我們參加了董事會會議,大聲疾呼,以確保其他塗鴉師和新晉塗鴉師有一個鞏固他們塗鴉權的地方。”
如今的索索迪夫塗鴉牆上可以看到一個名字:Sparky Z,他是亞特蘭大土生土長的塗鴉師,起步於1980年代,United Kings和Five Kings等團隊是那個年代的主導力量。當時的Sparky Z絕對想不到他的藝術形式有朝一日會受到推崇,他也從未期望過這一點,塗鴉師從不不尋求正統的認可。
然而,當亞特蘭大在1990年代為籌備1996年夏季奧運會而加大執法力度時,他開始看到許多朋友被捕入獄。
1993年前後,他放棄塗鴉,轉向音樂製作,同時在一家汽車輪轂店與另一位年輕藝術家艾米·謝拉德(Amy Sherald)一起工作。謝拉德當時是斯佩爾曼大學的學生,如今最為人所知的作品大概是為第一夫人米歇爾·歐巴馬(Michelle Obama)所作的肖像畫。
隨著他逐漸淡出塗鴉圈,他見證了這座城市如何將他和同伴們多年的塗鴉牆粉刷一新。他後悔當時沒拍下自己的作品,在那個時代,留下作品的照片就是留下了犯罪證據。
幸運的是,菲爾斯一直在記錄這一場景。1995年,他從克拉克亞特蘭大大學畢業,獲得歷史學學位,此後便留在亞特蘭大。若干年後,他在佐治亞州立大學獲得創意教育碩士學位,由此,他開始從在火車和建築物上塗鴉轉變為教授藝術字型塗鴉。
他是費金斯的紀錄片《眾王之城》的聯合製片人和主要解說員,Sparky Z也登上了這部紀錄片,由於在90年代初退圈,他已成為某種傳說。但菲爾斯成功說服他出山參與了拍攝,甚至激勵他在54歲的年齡重操舊業。
“因為這些人,我又回到了塗鴉圈,”Sparky Z說,“他們說,找了我30年。”
需要指出,塗鴉在亞特蘭大是非法的,違反該市的滋擾條例。但執法依賴於警察抓現行或居民向警方舉報。最近未發生此類情況,因為許多社區已經開始支援塗鴉。亞特蘭大警方曾一度將打擊塗鴉視為重要工作,現在已經允許在城市的某些區域塗鴉。
亞特蘭大公共事務官亞倫·菲克斯(Aaron Fix)坦承:“亞特蘭大有一些特定的自由區域,社區已經接納了公共藝術,比如克羅格街隧道。”
亞特蘭大交通網路MARTA的警察執法似乎也同樣寬容。過去5年,他們只逮捕了3人,都發生在2023年。但火車場和車站仍遍佈攝影機,警察會在這些區域巡邏,確保無人擅自闖入。
亞特蘭大及其他城市之所以採取了更寬鬆的態度,大概與時代變遷有關,相比塗鴉被視為破壞行為的年代,如今其價值已大幅提升。4月15日,許多人對帕蒂·阿斯特(Patti Astor)的去世表示哀悼,這位上世紀80年代的曼哈頓夜生活女王將尚·米歇爾·巴斯奎亞特(Jean Michel-Basquiat)和基思·哈林(Keith Haring)等街頭藝術家引入了曼哈頓的高端藝術區。
雖然這種聯姻未必適合其他城市,但如今在許多房地產市場最火爆的區域,塗鴉已經無處不在。在亞特蘭大的潮流街區,如西區、中城和克羅格區,遍佈塗鴉的啤酒廠、咖啡館和精品店的數量似乎與周圍房價的上漲成正比。
不僅僅是塗鴉。過去幾十年,社區對普遍意義的牆畫的興趣也顯著提升,它被視為了一種幫助新舊建築煥發活力的方式。備受歡迎的Living Walls系列推動了亞特蘭大各地牆畫的激增,展現了這座城市對時代精神的把握。從民權運動老兵和前國會議員約翰·劉易斯(John Lewis)到嘻哈傳奇Outkast等標竿人物的巨幅牆畫成為了深受全球Instagram使用者喜愛的畫面。
亞特蘭大的許多牆畫藝術家都是曾經甚至時下的塗鴉藝術家,他們將今天民眾對牆畫的歡迎歸功於塗鴉。塗鴉藝術家還教會了一些今天的牆畫藝術家如何從畫布過渡到牆面:使用什麼顏料,如何控制顏料不滴落線上條之外,以及如何最好地保護作品克服天氣影響。環線項目前藝術總監凱爾說這證明了雖然塗鴉曾經被貶低甚至定罪,但它為現代公共藝術運動奠定了基礎。
“我們希望證明對我們的文化景觀而言,塗鴉和街頭牆畫一樣重要且深刻,”凱爾說,“它們不是低端藝術。它們是公共空間和文化對話的重要組成,它們是城市公共藝術的先驅,毫不誇張地說,它們是全美各地公共藝術的先驅。”
當然,傳統塗鴉師與已經“合法化”的塗鴉師之間存在某種衝突,前者拒絕許可和利潤。幾十年來,塗鴉藝術家在躲避警察的同時完成了種種驚險之舉,包括在高樓、橋樑、廣告牌和路標上塗鴉,讓自己的名字閃耀在靠近天空的地方是他們獲得的唯一報償。
一些資深人士認為,那些經歷過奮鬥的人現在應當有權享受公共藝術行業的豐厚果實。
“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愛恨交織的感情,”Sparky Z說,“但與此同時,我想成為一名牆畫藝術家。我很高興它今天被大家所接受。所以我不會抱怨,因為這給了我們成為職業藝術家的機會,對吧?” (CITY來不)